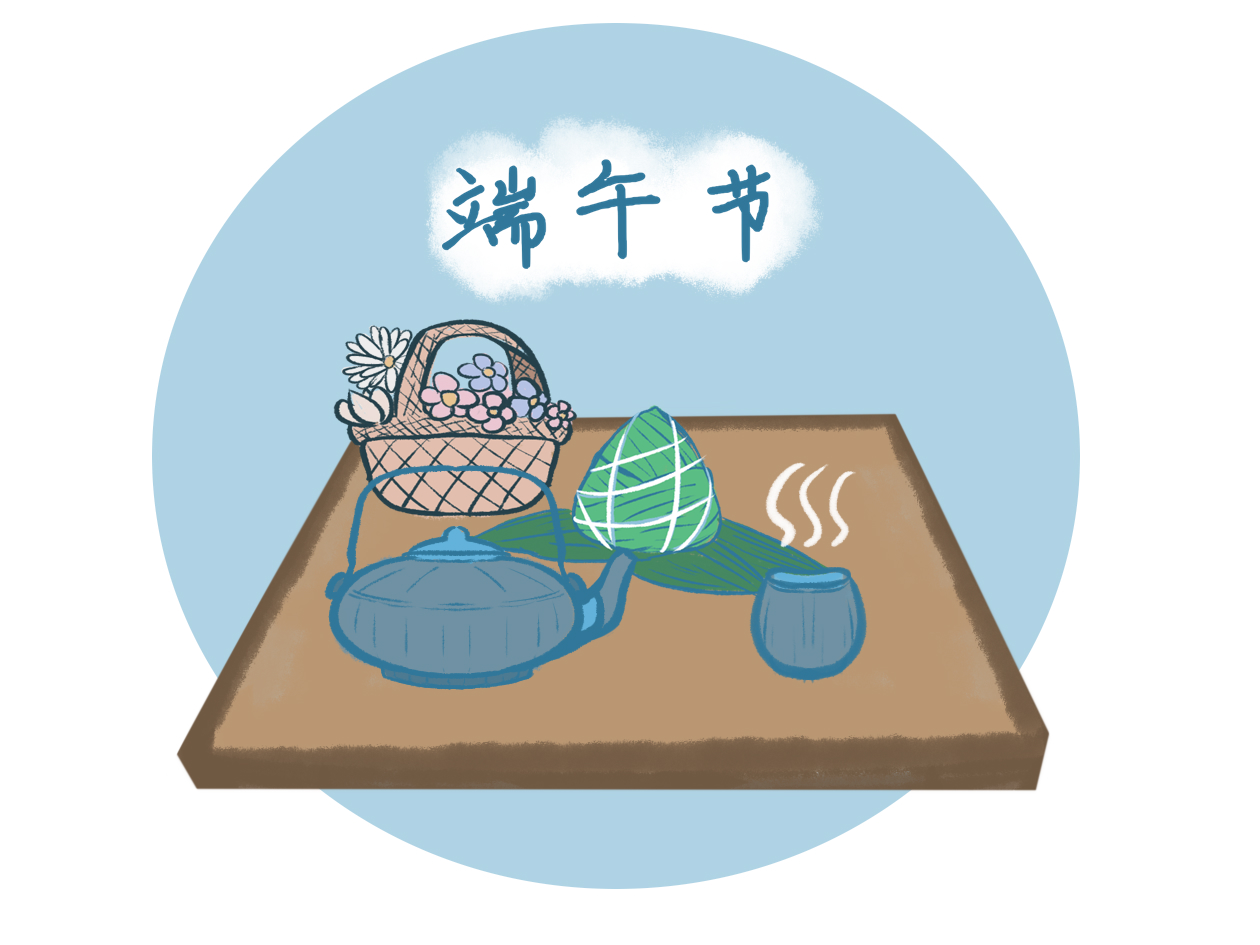爸爸点了一支烟,一缕阳光穿透空气爸眯起了眼睛。
故事已经破旧久远得厉害,若非我刻意问起,它们怕是要被彻底尘封
我幼时常盘了腿稳坐在祖父的眼上祖父吃一口饭,给我吃一口。虽则后来年岁大了,对小孙女发脾气也是常有的事但祖父是第一个宽容我调皮,情愿带我翻过沟去小卖部的和蔼亲人,我十分想念他。
在祖父的膝上已听了许多故事,关于曾祖父、曾祖母乃至祖父的故事,我都如数家珍。但相母一支的故事却知之甚少甚至祖母的姓名也不大明了,我不断深以为憾。大人们越是讳莫如深,我越是猎奇
终于爸喝了些酒,我凑到跟前问他可晓得他的外相家可发生了什么事么?怎样把祖母交给了我的曾祖母养?
我的爸爸先是不说话,略思忖了一会儿,气味幽微地浅浅道来。我听了许多,心绪交集,言语文字无法表明,只能浅白地讲讲了,且有几分真情实意也好。
故事自外曾祖父开始,传说他是极其霸道的人,村里人人敬畏。有时背着手慢慢踱步,若听人议论他,即便那声音窃窃,几乎听不到,外曾祖也会径直走到那人面前抬手就是一记大而响亮的耳光,那人大气也不敢喘一声。直到外曾祖冷哼一声鹅似的走去,围观者才敢稍稍松一口
外曾相大概是有些头脸,钱财上也不缺,解放之前就可以养活本人的五六个孩子,顺带还要将本人的侄子侄女养一起养活了,想来算是富有。然得意间太过嚣张,不知觉惹了村中许多人,众口铄金,言他是地主、是汉奸,生生欺侮至死,亲戚们都不敢替他买一口棺材,唯恐被他连累了去。同村有一老者,力排众议替外曾祖收了尸,买了棺材下葬。事情惨烈非常,我心里对此老者也十分感激,可以说是崇敬了。
外曾祖身亡,儿女们也接连被迫害做鸟兽散了。
外曾祖的大儿子,我应该称呼一声大舅爷,曾是受过些教育的,在国民军中是营长,因外曾祖之关系被连累,牵扯出人命官司,昔日也算出人头地的军官一朝成了阶下囚,在牢狱之中度过了漫长的十五年。妻带了一双儿女另嫁他人,大舅爷出狱被分至省城工厂唱工人,后来彻底无音无讯,不知他活了多大寿辰,死时可有亲友傍身?
最近的一次联系还是近三十年前,爸因不测身无分文,仓促间辗转寻了大果爷,舅苓吩咐逛一会儿去餐厅吃饭,但爸终也没有找到工厂餐厅,留易爷等了半响。傍晚爸赶火车,大翼爷送他,望着爸越走越远,直至再也看不见,此后再也没有见过家乡的任何亲人。那个时代,生离,也无异于死别。故事听到这里,爸和我都湿了眼睛。爸曾问罩爷怎样不同老家呢?舅爷摆摆手,一切尽在不言中,许是蹉跎半生,一事无成,既无法荣归,则此生不赴故里。
爸的三舅,是我三舅爷,小时害了眼,按现在说法也许是得了自内障,当时医疗条件极其不发达且无人照料,至于成了半瞎。外曾相目死,不超二十岁就盲了的三舅爷也去了曾祖母家,被我四姑奶揶
输捉弄,可见此等可怜人在那个时候其实
是无人可怜的。后来被同村人引至集宁让他本人寻生存的路去,一度去了张家口,刚好赶上了国家照顾残障人士的好政策,在工厂好歹有口饭吃。其实说是睡子,究竟也不是全盲,渐渐努力成了厂里主事的人,娶了妻,有了儿女。却说此时还活着,大概九十多岁,可一则路远无消息,二则爸并无十分钱财,终也不曾去探望三舅爷。
祖母是五官极周正的美丽女人,家破人亡之际无人照拂,无法间由曾祖母收留,不能说曾祖母没有私心,也许早在收留之际就想把亲外甥女嫁给本人的长子了吧。但在当时无人敢与外曾祖家有任何瓜莫的情况下收留外甥女,虽则有私心,大概也不算全无善心。
后来祖母和祖父勉强凑成一对,祖父脾气坏极,并不愿意娶本人的妹妹,但母命难违,另外娶妻实难,也就凑合了。祖父生得俊朗,人也聪明,在部队里认了字,二十一二岁从抗美援朝意愿军里逃了出米,出来,此事颇为人诟病,但我尚能理解他。
有三舅爷的关系,相父曾在张家口银行做账,但因缺了十二块钱被开除,后来又在张家口工厂里工作,彼时已经有了
四、五个孩子。刚开始祖母和曾祖母留在家乡村里,祖父在张家口工作。传说祖父有了相好,曾祖母含泪把祖母送走,至此祖父断了念想,但常与祖母吵架,家里并不太平。当时爸算是最小的孩子,赶上三年自然灾祸,只能买到代乳粉,爸哭闹得厉害,极其瘦弱,时到今日,骨瘦如柴。祖父出门在外,孩子又多,手里拿着钱也买不到半点粮食,一气之下带着孩子们回了乡里。大姑在火车上吃了些西瓜还是什么水果,回了村里闹肚子,祖父母有事不在家,曾祖母束手无策,九岁的大姑,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逝去
祖父的孩子多,早逝的也多,大伯四十八岁癌症去世,二姑四十八岁坠楼身亡。我爸第一个发现了二姑的尸身,忍痛另找人料理,担心祖父的身体,瞒了他把相父送回村里。我那时很小,并不懂什么爸爸回来了半天转头便走,走时眼眶红红的。祖父像是懂了,搂着我说"他们有事忙呢,其实我晓得,是二姑不在了。这几日都看不到她,我怎样不明白?"我看不懂他们的悲伤,自顾自由院里和我的狗一起玩泥巴。
我小时候生病,泌尿费劲,尿频且尿不出来,妈带我去县城看病,不是什么大问题,打几天点滴就好了,几日不回去,祖父以为他的小孙女也不在了,无法地敲着拐杖说“晶晶也死了。"言语上毫不避讳,但此时我似乎可以理解了。祖父已经被生离死别折磨得迟钝、麻痹,白发人送走许多黑发人,他的世界已经暗了一半,生命的逝去于他而言,已经很平常了
爸是很仁厚的男子。彼时四川女子动辄被卖到此地,爸曾买到肤白貌美的高个美女,但女子脾气倔得很,枕下常备剪刀。爸觉得留她不住,坐火车送走女子,女子请他吃了顿饭,挥手告别,也算是致谢。
有了这些故事,我像是寻到了本人的根,那个惨烈地为人迫害至死的外曾祖,揪得我心疼。
时代的巨轮不断在前进,碾死了外曾祖和大舅爷,但也究竟不是全无获利者,三舅爷和另一个当兵的堂舅爷在这个时代得到了应有的一切。
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时也,命也。我能做到的,只要铭记罢了。
上一篇:关于亲人离世的些许感受
下一篇: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