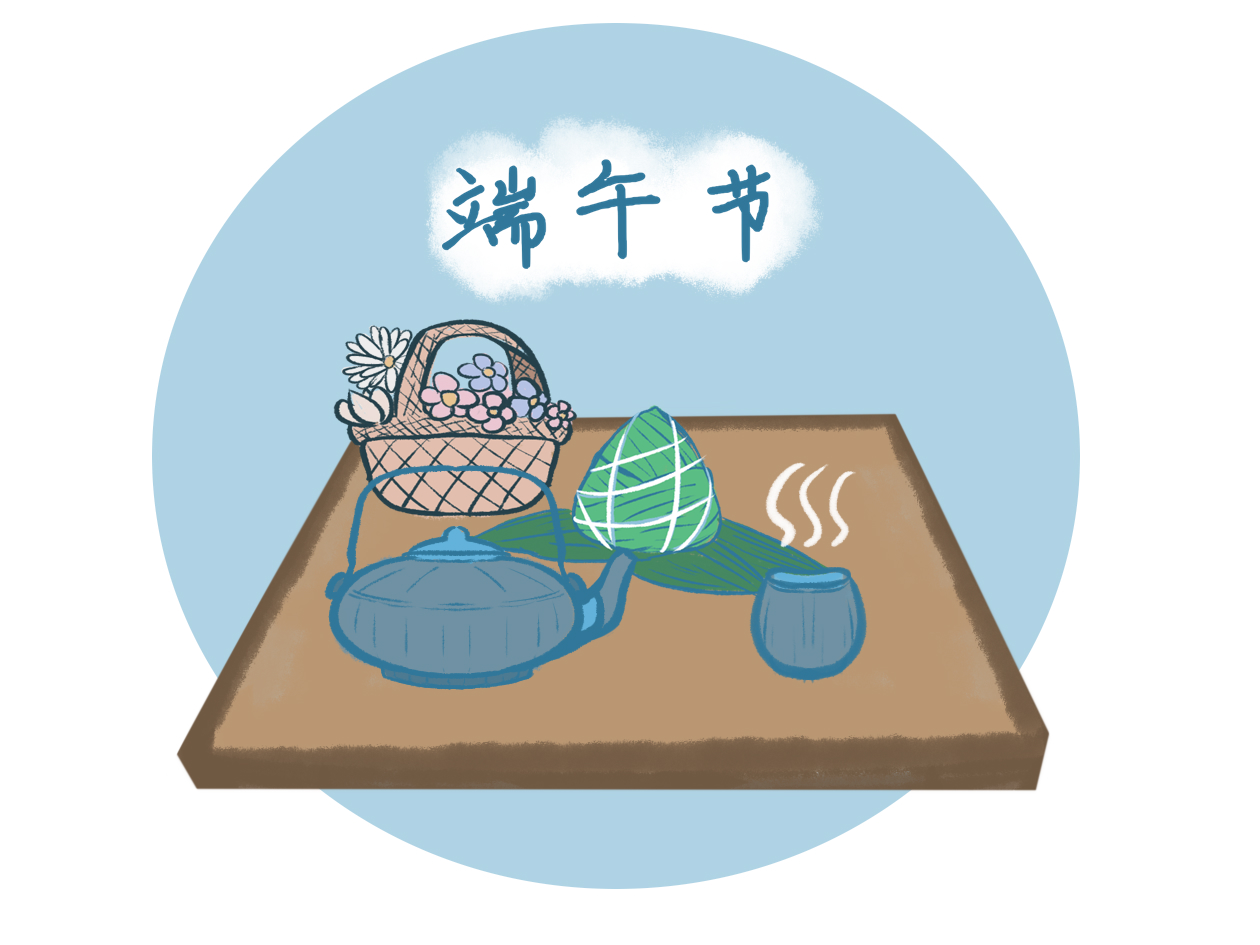刘艺/文
用这个题目做文章,很容易流于说教,如“人品高书品才能好”,“学书先学做人”等等。这些老生常谈很笼统,无法展开讨论。要探讨书品与人品的关系,须先从历史上作一回顾。
书品与人品不可分,自古就是这样认定。北宋欧阳修在《笔说》中讲道:“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然后世不推此,但务于书,不知前日工书,随与纸墨泯弃者,不可胜数也。使颜公书虽不佳,后世见者必宝也。杨凝式以婉言谏父,其节见于艰危。李健中清慎温雅,学其书者兼取其为人也。盖有其实,然后存之久耶。非自古贤哲必能书也,唯贤者能存尔。其余泯泯,不复见尔。”
这里举出了颜真卿、杨凝式、李健中三人,作为书品因人品高尚而名重后世的实例。颜真卿的事迹人所共知,可不详论;李健中是宋初书家,就现有材料来看并没有什么突出事迹,也可不论。对杨凝式则须作些引见。所谓“婉言谏父”是这样的:
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杨凝式三岁时,发生了黄巢起义。广明元年(公元880年)黄巢占领洛阳,国号大齐。僖宗逃往四川,各地藩镇自立,开始了由唐王朝向五代十国分裂时期的过渡。唐朝最初的皇帝哀帝(公元904至907年在位),不过是后来改国号后梁的军阀朱全忠的傀儡。哀帝天佑二年,杨凝式的父亲杨涉担任了宰相。这年杨凝式已三十三岁,获进士及第第三名。天佑四年,哀帝将皇位“禅让”朱全忠,为此任命杨涉为“押传国宝使”,将唐朝传国八宝献给朱全忠。杨凝式得知后即谏告其父说:“大人为唐宰相,而国家至此,不可谓无过。况手持天子玺绶予人。虽保富贵,奈千载何,盍辞之。”杨涉闻听大惊,忙申斥他:“汝灭吾族。”传说杨凝式听到父亲的怒斥,心中害怕,即刻佯狂,所以又有“杨风子”之名。
杨凝式婉言谏父,在封建社会被认为是难能可贵的好品德。在书法上,他受颜真卿的影响,是由唐入宋的枢纽人物,在五代文运不振的时期,维系了我国的书法传统。由于有谏父的美名,书品更被高度评价:“杨少师劝其父不以社稷予人,此与鲁公拒安禄山、斥李希烈何异?故其书虽承唐末五季馀习,犹有承平纯平气象。此侍御帖乃有鲁公座位帖笔法。论书当论其人,工拙不足论也,况其工如是。”(《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二十《题杨少师侍御帖》这里几乎将杨凝式与颜真卿等量齐观。其人伟,故书品自高,何况其书甚工呢!
颜真卿、杨凝式的例子,可以作为我国古代书品与人品相关联的正面代表。与此相反,反面的代表则有人提到过元代的赵孟頫和明末的张瑞图、王铎等人。赵孟頫在元代文艺冷落时期,复活了以王羲之为首的晋唐书法,创造了平实稳妥的书风,已经风靡一时,在书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但由于他是赵宋的贵胄却在元朝担任要职,故被后人视为节操不好,人品欠缺,因而书品也遭到贬抑。一般认为,赵字甜俗,似有媚骨,所以有些人不喜欢赵字,不愿学赵书。明末,张瑞图、王铎的书名很大,书技极熟,但遭到人品的影响,在历史上不为人所重,或受人厌弃。即便在颇爱张王书法的日本,也有独具见解的学者批评说:“至于张二水、王觉斯辈,彼邦(中国)稍有气概者,犹耻藏其迹。而我邦则兼金竞购,生怕或后,诚不知其何心?小栗秋堂老于赏鉴者,其所珍藏,皆珍若球图,精善无匹,不俟余言。今影印其数十事以颁同好,意至美也。宜独标别裁以一新耳目。乃犹著录张王诸人之迹,以徇流俗之好,何哉?固书以问秋堂。”这是日本著名学者、书法家内藤湖南在1915年应珍藏家小栗秋堂之请,为他的藏品图集所写的《苏竹墨缘序》中的一段话。这里把张王作品视为鄙俗之物,在替人作序时竟向该人提出质问,这是极少见的。
以上举出的正反两面的例子,说明古人对人品的评判是就大节而言的,即指封建社会中最大的节操——忠君而言的。颜真卿、杨凝式忠君爱国。其人品最高,书品也因而高迈,受人尊重。赵孟頫、王铎等人仕奉两朝,是谓“二臣”,节操不佳,书虽巧,书品却不高。其余未显出大忠也不见大不忠的数不清的能书者,字与人一样不引人瞩目,书随人而逝,泯灭不传。这就是古人评论书品与人品关系的根本观点。与其说它是一种道德观,还不如说它是评价书法的“政治本准”。在历史上人如潮涌、书如烟海的中国,首先根据这条标准肯定或否定那些代表性的书家,是必然的,笼统的优劣好坏是没有的。但是,古人这个品评人物与书法的观点,今天能否仍然无效?
我国今天的情况与过去大不一样了,社会制度变了,道德原则也不同了。然而,对书家和学书的人来说,书品与人品密不可分,这一点并没有变。现今,具有高风亮节,受人民崇敬的人物,其书作也被视为瑰宝,片纸只字,都是价值很高的珍藏品。给人民带来浩劫的奸佞之徒,虽极力附庸风雅,假冒斯文,甚至遍地题字,标榜左笔,但人民恨其为人,也鄙视其书,书与人俱为人民所不齿。这一现象,几乎和过去没有两样。但是,今天评价人品的标准,已不同于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现在是由个人在历史前进的轨道上所起的作用,来判定他的好与坏、忠或奸,从而对其书品给予褒或贬。但毕竟从表象上看,我们今天对某些人其书品与人品之间的关系的分析和认定,与古代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都具有强烈的人格主义倾向。这带有民族色彩,并反映了书法在中国社会及人民意识中的特殊地位。
可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能够举出的书品因人品而遭到褒或贬的人,都是地位较高的人物。只举出这类事例,对今天探讨书品与人品的关系问题是不够的。因为绝大多数写字的人,人品没有什么突出之处,他们书品与人品的关联不能用大人物的模式去套。
广大书法家和学书的人,其书品与人品有什么关系?怎样来认识这个问题?回答这些问题时,很容易简单地搬用本文开头举出的老生常谈。但泛泛之言是无济于事的。譬如“学书先学做人”,少年学书者有这样的愿望当然很好,然而怎样“先学”?“做人”达到什么程度才能开始学书?这些都是无法回答的问题。因而,广大书法家与学书的人要从本身的实际情况出发,去认识书品与人品的关系。首先该当承认,每个人的书品是有高下之别的。这种差距是技术缘由形成的,还是与人品有关?这样探讨,就会把书品与人品的关系问题搞得深入一些。
既然每个人的书品有区别,那么怎样分析和评定一个人的书品呢?古人对此提出过精辟的见解与标准。北宋朱长文的《续书断》中,将初唐至北宋的书法家作品,分为神品、妙品、能品三类。这三类虽然等级不同,但都属于书品高尚或良好的范畴,其划分的依据与书家的人品分不开。比这种评价方法更为简明概括的是,将书品分为相对的两大类,即俗与不俗这两类。北宋黄山谷等人,不只在书法创作方面,而且在题跋及书论方面,都在书法史上留下了辉煌的记录。黄山谷评价书品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以俗与不俗为分野。他已经说:“近世唯颜鲁公、杨少师特为绝伦,甚妙于用笔,不好处亦妩媚。大抵更无一点一画俗气。”(《山谷题跋》卷七《论书》)他还说:“一见颜鲁公书,则知欧虞褚薛未入右军之室。见杨少师书,然后知徐沈有尘埃气。”(同上卷四《跋王立之诸家书》,徐沈即徐浩、沈传师。黄山谷在他那个时代,屡次举出颜真卿、杨凝式为不俗的代表,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是一个人格主义者,书法上又学过颜、杨的行草书,故对此二人有特殊好感。
俗与不俗,不止是宋人评书的大准绳,而且沿用至今。我国现今的书法活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沉寂后,开始活跃起来,出现了“书法热”。全国各地男女老少对书法有兴味的人很多,涌现出一批新人和佳作。但通过各种书法活动也可以明显看出,不俗的高格调作品尚少,粗俗之作则较多。作俗书的缘由很多,但总的来说是与作者的人品分不开的。这里讲的人品问题,不同于前面所说的大节问题,而是属于修养与造诣的问题。人们由于思想修养、道德观念、审美情趣、学识水平、性情爱好等方面的不同,决定了各自客观条件的差异。各方面造诣高的人,人品格调趋于高尚,学书作字不易流于鄙俗。相反,客观造诣不高的人,其精神格调也不可能很高,作书习字难免粗俗。至若把书法当作获取名利的工具者,其书品不只是俗,甚至是恶,这一点又当别论了。本文虽然是谈书品与人品的关系,但只是讨论一般人的情况,现实生活中的极端之例,不言亦可明其性质,故不需赘言。
总之,只需细心观察各类作品,就不难窥出其书品高或不高。总之,只需细心观察各类作品,就不难窥出其书品高或不高,俗与不俗,并可据此推测作者的人品格调及修养如何。达到了这一步,就不难理解书品与人品在一般书家及学书者身上表现出的因果关系,从而注重加强本人的人品修养,包括思想与学识等方面的修养。在此基础上,留意使书品逐渐脱俗,转向高迈,那么,日常的砚田笔耕将更富于情趣,将能创作出更多的好作品。对于广大书法家及学书者来说,讨论书品与人品的关系问题,其现实意义大抵即在于此。
刘艺(1931——2016),原名王平,别署实子。客籍台湾省台中市。著名书法家,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创作评审委员会主任等。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此文选自孟云飞主编《翰墨人生》,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