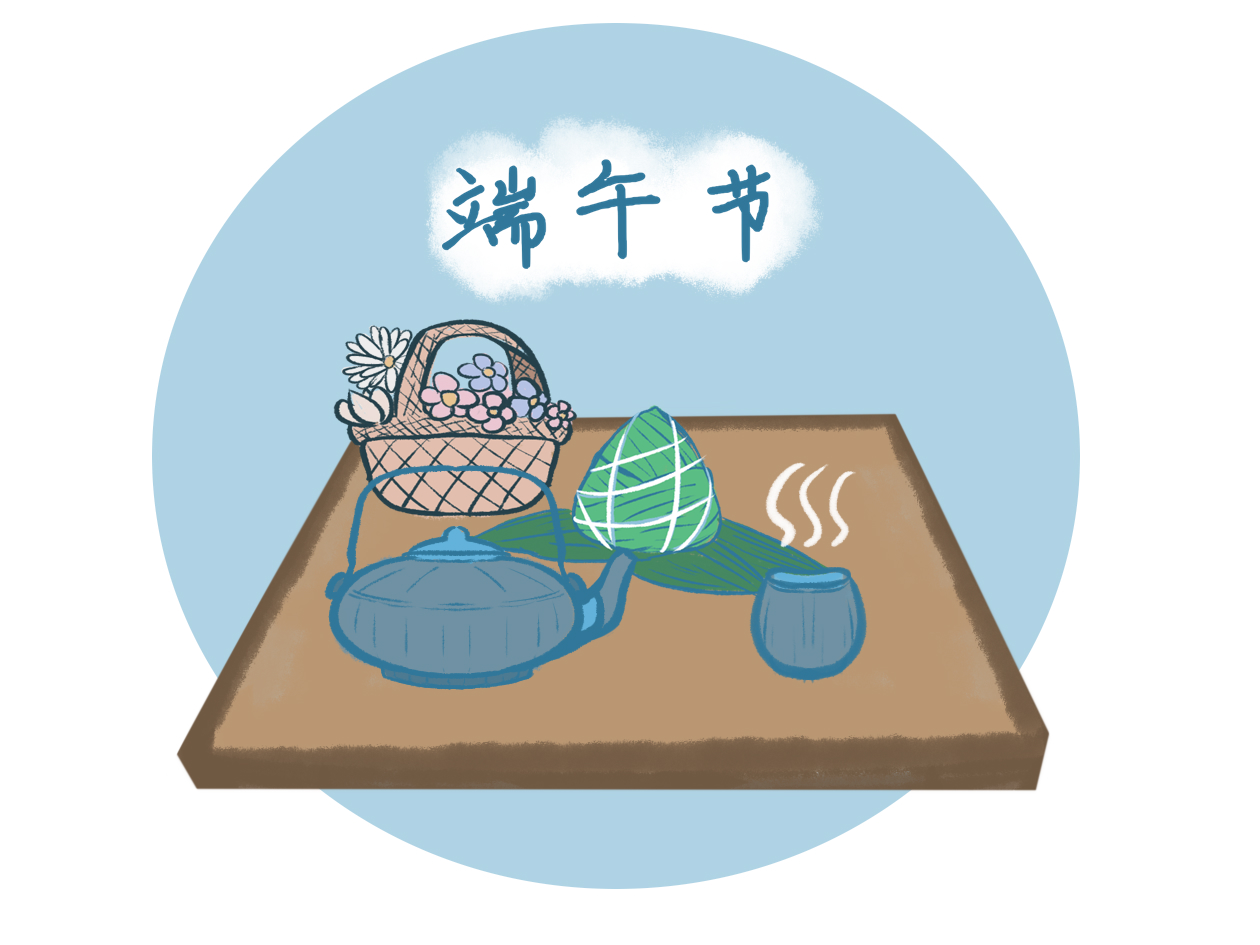《误拾的私印》
------------文章来源自知乎
大魏名门贵女无数,我一个落魄世家的庶女,如何都是配不上裴恕的。
但我仗着裴恕战死,拿着误拾的私印面圣,婉言本人与他早就互许了终身。
我成功当上了青阳王裴恕的遗孀。
可如今,我那骗来的死人夫君竟活着回来了。
1
我那位已死数年的夫君突然活了。
他回来的前一夜,我收拾包袱打算连夜逃出青阳王府。
府中的院墙甚高,我顺着院墙边的老槐树颤巍巍地往下爬。
彼时正是月黑风高夜,眼见我即将落地逃离我那夫君的魔爪时,有一只手在树下恰好抓住了我的脚腕。
那手冰冰凉凉没什么人气。
深更半夜还在外游荡的定不是什么正派人,我一时间汗毛直立,直觉是撞了鬼。
惊叫一声,攀着树干的手便这般松泛下来,在我即将从树上摔下时,身后那双手先是拖住我的腿继而搂过我腰身将我整个人抱进怀里。
那人怀抱甚是宽厚,力气该当也不小,托举着我,低头间呼吸喷薄的我面上微痒。
身上还有热乎劲儿,是个活的。
我以青阳王妃的身份横行霸道了整整三年,自是不会惧一个半夜在王府院墙外游荡的贼人。
颐指气使的姿势一上来,毫不客气地踹了面前人几脚,狠狠拍他的手,恶声恶气地朝他低声骂道:
「哪来的登徒子,快把你的脏手给拿开,信不信我让府里下人打你板子?」
一声低笑骤然响起,显然那人并未将我的话当回事,他依旧箍着我,还腾出一只手挑衅般的薅了把我的头:
「深夜外出是迫不及待来见为夫的么?」
「别瞧我生得好看就想占我便宜,你……」我话未及说完蓦然住了嘴,意识到什么般,提着手上风灯靠近面前男人的脸。
借着幽幽灯光,大抵看清面前男人的容貌。
轮廓坚毅,眉目凌然,赫然就是我那死了数年的夫君青阳王裴恕。
惊吓太过,手中风灯随即掉落于地,我当即成了被猫捏住要害的老鼠,彻底蔫吧了,瑟缩着身子转口就跪了下来:
「是妾身贪图富贵,一时鬼迷了心窍,所有罪妾都认了,求青阳王饶了妾一条性命。」
我抱着裴恕的腿,比当年在裴恕灵堂上嚎得更为悲切。
2
青阳王裴恕是什么人?
新朝未立时是枭雄,是霸主,割据一方自是无限风光,战场上亦少有败绩。
这大魏的河山是裴恕打下的,至尊之位亦是他不屑去要拱手相让的。
新帝登基后,他封侯加爵,权柄傍身,就连皇帝都要敬上他几分。
说实在的,大魏名门贵女无数,我一个落魄世家的庶女如何都是配不上青阳王的身份的,然而人嘛,被逼至极处难免会干一些荒唐事儿。
三年前我那懦弱无能的亲爹要将我嫁给某位上了年纪的老知州做妾,我那会年方十七,娇花似的年纪,自然不情愿就此插在那坨老牛粪上。
索性讹上了正办着白事的青阳王府。
裴恕那一年自请去平定新野叛乱,遭叛兵偷袭,外加旧伤复发,死在了这场围攻之中。
死状甚是凄惨,尸体被抬回都城时已然面目全非。
我拿着旧年战乱时在苍州机缘巧合下误拾的一枚私印去了青阳王府哭丧,婉言他裴恕旧年与我有过一段不为人道的情事,早早就互许了终身,这枚印信自是凭证。
也许是因为我说得情深意切,裴恕旧日的部下都对此事深信不疑。
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哭着言我生是他裴恕的人,死是他裴恕的鬼,就算他如今不在了我如何都要嫁给他。
裴恕是一国功臣,如今他一死啊,自是以皇室之礼厚葬,百官素服七日,皇帝更是亲至奠醊。
既是功臣,自该服从他生前之愿。
这事儿传至皇帝耳中,当即就下旨给我同裴恕赐了婚。
我就这般逃过我爹的魔爪入了那青阳王府,成了青阳王裴恕的遗孀。
既免了为妾的凄惨命运,还借着裴恕旧日功绩横行霸道三载不足。
我承认我是个骗子,贪图安逸,骗了一个已死之人的正妻之位。
如今我那骗来的死人夫君竟活着回来了。
我同他素不相识,更别提情根深种互定终身,他一旦将此事说破,指不定我就要被安上个欺君之罪,脑袋分家。
我本想连夜跑路,不想正同我那冤大头夫君撞了正着,本欲哭着认罪,可裴恕却未曾追查我,反顺着我话道:
「你这姑娘啊是该认罪,明知我已身死,大好年华非要空耗在我这么死人身上,着实脑子不太好使。」
我哭了一半硬生生停在那儿,呆愣愣看着他,而他也浑然不客气,拎鸡仔似的将我拎回了王府。
说来惭愧,死而复生的青阳王回都城的第一日,便让为他守寡三年的王妃跪在祠堂软垫上,抄了十遍兵书。
3
天无绝人之路,裴恕做这一切的缘由是他失忆了。
他声称三年前遇袭时伤了头部,丢了所有的记忆,这些年慢慢找回一些,却还忘了关于我的所有。
裴恕以为我已经同他有过那么一段,如今教训我亦当真因为恼我当年不顾一切嫁了他。
俗话说得好,爱之深,责之切。
虽说他的爱未必有多少,但他教训我倒是真心实意。
他婉言以他往日在军中的性子,应该赏我严严实实二十军棍,但思虑到我是个姑娘家,几棍子下去也许人就没了,索性罚我抄些兵书让我长长记性。
这些年我仗着他青阳王府的势过得不算坏。
见天儿的看戏听曲观灯赏花,平日话本没少看,亦有样学样胡编了不少我同裴恕的过往,由得都城之人津津乐道。
日子太过安逸,难免不太能吃苦。
兵书未抄上几遍,我腿麻,手腕亦疼了起来,自顾不得裴恕是什么洪水猛兽了,坐在软垫上同裴恕哭着求了饶。
裴恕哪怕失忆,也着实算不上什么温柔解意的性子,毕竟草莽出身一武夫。
本在一侧撑头看我笑话,听得我哭,遂起身走到我跟前蹲下,问道:「当年既有嫁我的勇气,怎生罚你吃些苦头就给哭成这样?」
「你以前可疼我啦,舍不得我受一丝苦,成日将我放手心捧着,我何曾遭过这罪?」
我揉着发疼的手腕,毫不犹疑地开口胡诌。
裴恕显然不信,用袖子擦花了我的脸的同时,颇为狐疑地瞅着我:「当真?」
我实在瞧不上裴恕甚大的手劲,狠狠甩了甩头,叉腰拿出恶猫瞪虎的架势,恨声道:
「你成了个死人我都闷不吭声嫁了,还能诓你不成?不想要我便直说,又是罚跪又是抄兵书,当年跟你好上的时候你哪舍得这般待我?」
总归裴恕不记得了,我为保命欺他一时也实在没什么错处。
「都说当年乱世未平,苍州初遇,我一个军中粗人同一个小姑娘好上了,骗人身,骗人心,还留下印信婉言天下大定后求娶于她,如今想来……」
他也不再有罚我的意思,扶着我的腰一把将我捞起,起身推门抱着我离开祠堂。
只是话说了一半顿在了那,着实让我心焦。
我遂匆忙问道:「如今想来什么?」
他带着我融进夜色,低笑一声:「如今想来,我并不好女色,更不可能困囿于儿女情长,温霁,你莫不是在诓我?」
这桩婚事是当年我强求来的,不过是欺他裴恕已死,无法再开口生言。
我笃定了死人是不会为本人的洁白与否辩驳半分的,索性将裴恕的名声霍霍个彻底,因而哪怕裴恕盖棺后功名加身,倒也落得一个喜爱少女的荒唐名声。
心虚是一回事儿,我若真顺着他话来,遭罪的定然是我。
他将我抱至屋内,放在榻上,彼时我心中那点畏怯早早消了干净,拽着他领子,掰足了气势道:
「裴恕!是不是你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以前的所有承诺都不作数了?这世上哪有你这般混账的男人!当年我瞎了眼才跟的你!」
想要将人给骗过去,我这戏自然要演的有几分真,于是我瞅着裴恕倒也吼出几分真情实感,竟当真冤枉上了。
裴恕看戏般的,眼中划过几分玩味,直到我止了声,才不慌不忙地在我面前伸长了手:「别嚎了,大半夜的不嫌聒噪,先过来给为夫宽衣。」
我眼中尚含着泪,口中未竟的话被裴恕这一声给阻了,我抬头愣愣看他,裴恕自立于原地岿然不动的同我对视。
「你……要睡我这?」我没了方才的气势,讷讷问道。
他轻笑:「怎样?既已嫁给我,让你独守空闺这么些年终归是我的错,如今我回来,也该补你一场洞房花烛。」
「不行!」我想都未想便道,还不忘往塌里缩了缩。
裴恕一副了然容貌,在我心虚的同时慢吞吞开了口:「既有夫妻之名,分房而睡终归不妥。」
「谁让你死了那么多年又突然回来,我还没预备好……」我声音细弱蚊蝇。
他见我未动,倒也不恼,兀自解了腰间系带,褪了外袍,也未上前,只意味深长瞅了我一眼:
「刚才吓唬你的,我睡外间榻上,不会拿你如何。」
裴恕说完,也当真出了内屋,我缩在榻上一角,只瞧见灯火投映在窗棂上的一道影子,不多时外间灯火也熄了。
他隔着一道门却还不忘嘲笑我:「你这孩子胆子这般小,老鼠似的,当真不经吓。」
4
当年新朝初立,裴恕没做这皇帝,甘为人臣,总还徒惹不少忌惮。
那会朝中尚有不少投诚的旧朝臣子,被裴恕这么压制着,哪怕前朝风光一时,在如今的朝堂上却也如何都翻不了身。
就算军功赫赫,裴恕既没当皇帝,便总要落得一个功高盖主的诨名。
于是裴恕就这么死了,死的还正是时候。
如今他活着回来,裴恕混不知收敛二字如何去写,依旧是过去的做派。
裴恕以前爬得太高,自然眼高于顶,不屑将任何人放在眼里,哪怕是当朝的天子。
不只佩剑上朝,见到皇帝礼都未行,当朝被那群文臣呵斥时连眼亦未抬,只不咸不淡道:
「当年本王行军北上时,尔等一干文臣却只知战战兢兢龟缩一隅,口诛笔伐是打不下这江山的,如今天下大定,各位耍着嘴皮上的功夫,不若省些气力。」
他这话说的甚是猖狂,朝中那些文官近些年安逸惯了,又何曾受过此等侮辱,哭嚎的哭嚎,撞柱的撞柱。
老丞相更是指着裴恕的鼻子大骂其狼子野心,当时就气得撅了过去。
于是裴恕才回都城数日,就被皇帝找了个理由打发回去休养生息,听说每日参裴恕的折子堆的足足有半人高。
那会我正躺在屏风后的摇椅上,听院中躲懒的小丫鬟讲这几日的朝事,面上盖着新进的话本,悄无声息地装死人。
外边正讲到裴恕当年入主帝都前那场仗。
前朝那破落君主在都城将破时,将那些世家贵族的女儿们推上城楼做人质,裴恕的兵往前行进一步,便杀一个人。
裴恕未曾罔顾人命攻城,反倒在试图救那些女眷时,遭人暗算受了轻伤。
再而后裴恕未霸着帝位,而是拥了当今圣上登基,继而又在新野身死。
世人都觉得以裴恕的性子,这帝位让的莫名。
便也有人归咎于他当年所受的伤上,都言他裴恕命不久矣因而才弃了这帝位甘为人臣,新野一战又恰巧因牵动旧伤而丧了命。
然而裴恕如今尚还活得好好的,说明世人所言亦大多不可尽信。
我听那几个丫鬟七嘴八舌地讲述裴恕的过往听得正尽兴,偏在下一刻齐齐止了声,而后又是颇划一的下跪声。
自以为是我发出动静惊到了她们,只随意隔着屏风道:「不用顾忌我,接着说。」
于是屏风外又是阵阵抽气声。
我又听得有脚步声绕过屏风而来,一把就抽走了盖在我脸上的话本,声音亦含了笑:
「我当年建府未有多时便离了都城,那会好歹府中规矩也算严明,如今不过数年,王妃这懒散性子,连带着整个府上都惫懒起来。」
裴恕前几日让我罚跪,还吓唬我要我伺候他行房,我如何都忍了,如今偏还甚会在鸡蛋里挑刺儿,怎样看都浑似故意要瞧我的笑话。
「我年岁本就小,管不好这府中事务。」
我怯生生开了口,又伸手拽他的袖袍:「你这些年又不在,我思及旧人时也只能在旁人口中听些你的过往。」
「哦?」
「妾的夫君是平乱的英雄,世人口中的传奇,听旁人说上你多少遍我自是听不腻的。」我想都未想,张口便道。
裴恕愣了愣,须臾望来时眼中似如何都化不开的浓墨,衬着他那肃然冷冽的眉眼,让人心间空冷冷的颤了一下。
他说:「我如今回来了,你想晓得什么,问我便是,夫妻之间本没什么不能言的。」
「攻入都城前,究竟是谁伤的你?新野一战你又为何会假死?」他既松口让我问,我亦毫不客气地婉言。
他显然没料到我问的是这个,想都没想便道:
「伤我之人只是旧识,我这人记仇,当年便已将仇报了,新野一战她们说的亦不错,是我因旧伤未愈而败,亦因而一役忘了一切,不再困囿于朝堂权势。」
我遂也伸手捶了他几下,呜呜咽咽开了口:
「这些年,你这混没心肝的分明什么事儿都想起来了,偏将我忘了个干干净净,我瞅你分明是在外面有了相好的,回来骗我说失忆,好娶你那位藏在外面的娇娇娘子。」
我从来不怂裴恕,在裴恕面前总有那么几分无理取闹。
毕竟他旧日也是个位高权重的主儿,好面子,心中自然对世人言他喜欢少女这事儿颇为膈应。
他失忆了,对我的话全不曾尽信。
我要让他相信我爱他,相信我同他真逼真切有过那么一段,因而在他面前如何都不能表现得太过生疏。
裴恕对我这一招似乎颇为受用,他长长喟叹一声也顺势将我半搂在怀里,轻拍着我后背似在耐着性子哄慰我,他说:
「当年忘了一切,不困囿于朝堂权势,这世上其实是有许多地方可以供我去的,你也莫要难过,我既回来了,便没有不要你的理由。」
5
近些年,我同裴恕的旧事在都城被绘声绘色传了个遍。
光我所知晓的便无数十个版本。
茶楼里的先生言裴恕当年在苍州遇上战乱中同家人失散的我,他见我恰是豆蔻梢头的好年纪,又瞧我柔弱貌美娉娉袅袅,三言两语将我诱哄了去同我私定了终身。
戏院里的戏子咿咿呀呀,不知为何偏也编了出爱恨情仇的戏码,还言我同裴恕种种磨练后互诉情义以身相许,而后新野一战生死离别,又是一番哭断肝肠。
独一自我口中传出的版本,是我口述让坊间书生写得话本。
我编的这段故事终归太过胡扯,旁人只将这话本当成一段戏说,宁可去信那些个说书唱戏的,也不曾信我这正主亲口说的这段过往。
裴恕也许旧年受伤当真摔了脑子,回来后虽说得罪了一众文臣,倒也不再醉心权势,当真称病了一段时间做着他的闲散贵人。
于是乎,还花了几天将这几种版本的故事瞧了个齐全,最初还将那替我写话本的书生给抓了回来。
裴恕的副将在一侧读军令般一板一眼地读着话本。
军中的大老粗,不时还会读错上几个字,听得人甚是膈应,书生则发着颤跪伏在地涕泗横流地哭着求饶。
唯独上首坐着的裴恕,饮着他的茶,泰然自如地听着,不时还会发出几声耐人寻味的笑。
世人都怕裴恕只要我不怕。
哪怕他想起一切晓得真相,他堂堂青阳王再好面子也自不屑去寻我一个姑娘家的麻烦。
我进来时瞧见书生的怂样,不轻不重踹了他一脚,轻斥道:
「出息,这本就是我同王爷的过往,你照实写下,又有什么怕的?王爷还能将你吃了不成?」
他遂又哆嗦了一下,头埋得愈发低了。
「过来。」裴恕便在此时同我招了招手。
我径自上前坐在他身侧,还不忘给本人倒了杯茶,连珠炮似的道:
「这世上没人比我更清楚那些旧事,王爷说过夫妻之间本没什么不能言的,何必绕过我自行去查探过往?」
我气鼓鼓瞪着他。
裴恕也没恼,反栖身向我靠近,言道:
「这些年你我二人的旧事在都城被传得轰轰烈烈,我逐个听来偏全无什么感觉,反倒是这白面书生写的话本让我有几分猎奇,遂将人抓了来细问,不想竟是阿霁你亲口所说让这书生加以润饰的。」
他离我极近,就这么大剌剌瞅着我,不及我回应他,他却又道:
「当年我中了埋伏掉进江中,是阿霁你以为我要轻生将我拖上来的。」
「对我一番劝慰的是阿霁你,陪着我在苍州小城的是阿霁你。」
「我被你所救心存感激,又在你悉心照顾下,对你心存爱意,苍州多山樱,我日日总会摘上一束山樱放你屋中。」
「那会你年纪小,自受不住我这般的浓郁爱意,一次又一次将我给推了出去,我使尽解数,同你说尽情话,许尽誓言,到底让你将一生托付给了我。」
「想来,我的好阿霁啊,我当是极爱你的。」
我脸皮再厚如城墙,也被裴恕这一连串的话给说得薄了一层,我颇不自由地看向别处,轻声道:「当着那么多人面说这些,你害不害臊!」
话本瞧多了,有些故事倒也能信手拈来,我当时骗书生帮我写这话本时,不过是深闺无趣,图个一时之乐,如何都未曾想到裴恕能活着瞅见这话本。
而书生又是个深谙风月事的,写的话本比我所述多了不少昳丽矫饰。
一心征战夺取天下的枭雄偏被这书生写成了满口情话只顾情爱的痴汉,裴恕是老虎而非病猫,如今定然也是压着一层怒火的。
不然这落魄书生也决然不会被裴恕的气势所威慑哭得活像死了爹娘。
裴恕身边那没眼力见的副将依旧用那平的没什么崎岖的音调读着话本,正读到一段话本里裴恕所说的情话:
「我这人总归是有一二私心的,既盼着你爱我,又担忧你因我爱太满而厌恶于我,贪欲初生,总免不了一番挣扎,若能及时止损,一切尚有回转之机时,我尚能放下,可拖到现在爱意滋长,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是你,我这辈子必不会再有回头路了。」
我羞得用袖子遮住了脸,而裴恕在止了那位副将继续读话本后,毫不客气地将我胳膊扯了下来,反问:「这是你说给他写下的么?」
他未曾问能否为他过去所言,亦未曾发怒,倒问了这莫名问题。
习武之人手劲大,我被他抓着的手腕轻轻发疼,想往回缩,他却如何都不曾松开半分。
偏那呆货书生嘴欠,见我俩僵持,忙哭着承认:「此话是王妃……」
「你抓疼我了!」我未让书生将话说完,蓦地同裴恕喊道。
说来,他回来这些日子,我借他失忆,欺他骗他,瞎话信口就来,都不曾心虚半分,偏在这时生出了心虚之意。
而裴恕到底松了手劲,再我又一次想挣开他逃开时他却说:「这个故事我有印象,这话我似乎亦曾听过。」
「何时听过?」我问。
他轻轻弯了眉,一身坚冰戾气霎时化了大半。
他半晌才言:「故人入梦时。」
6
话本里的故事,若说真,其实大半竟是假的,若说假,却也不尽然。
我年幼同裴恕的确曾有过一段交集。
是裴恕从江中救下的我,硬缠着裴恕留在苍州的是我,日日摘山樱送他的是我,说尽情话,许尽誓言,要将一生托付给他的同样是我。
年少慕艾而已,他这般的大人物大抵在未失忆前便早早将我给忘了个干净。
裴恕这人啊,有雄心野心,亦有收兵略地,收复天下之能。
他本是军妓之子,一个女人在军营里瞒过所有人拼死生下的孩子,本来一出生就该被扔下自生自灭。
可裴恕天生命硬,不只活了下来,年少时又得前朝车骑将军孟梁青眼收作义子。
习武不辍,用兵如神,也曾打过无数胜仗,偏生在乱军起义后的长兴之战中倒戈。
那本就是个乱世,但凡有能之人皆能将手中刀剑对准那本就无能的王朝,而裴恕从不愿屈居人下,野心本就昭然。
他连占北边数座城池,甚至婉言要翻覆整个王朝成为这天下共主。
当年各世家于烽火过处举家迁往帝都,裴恕的兵攻往岷川时,不顾守城将领开出的条件,欲强行攻入岷川,逼得驻守城池的士兵四散溃逃,在城中四处烧杀抢掠。
温家早早收到消息连夜收拾细软欲举家逃往帝都,我爹怕车马脚程慢,遂将我连同十数位婢女弃在了岷川。
我本就是一个不受宠的庶女,十数年住在偏院向来无人问津。
什么因乱世与家人离散皆是假话,我从来都是被弃掉的那个。
-本文来源自知乎《误拾的私印》
下一篇: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