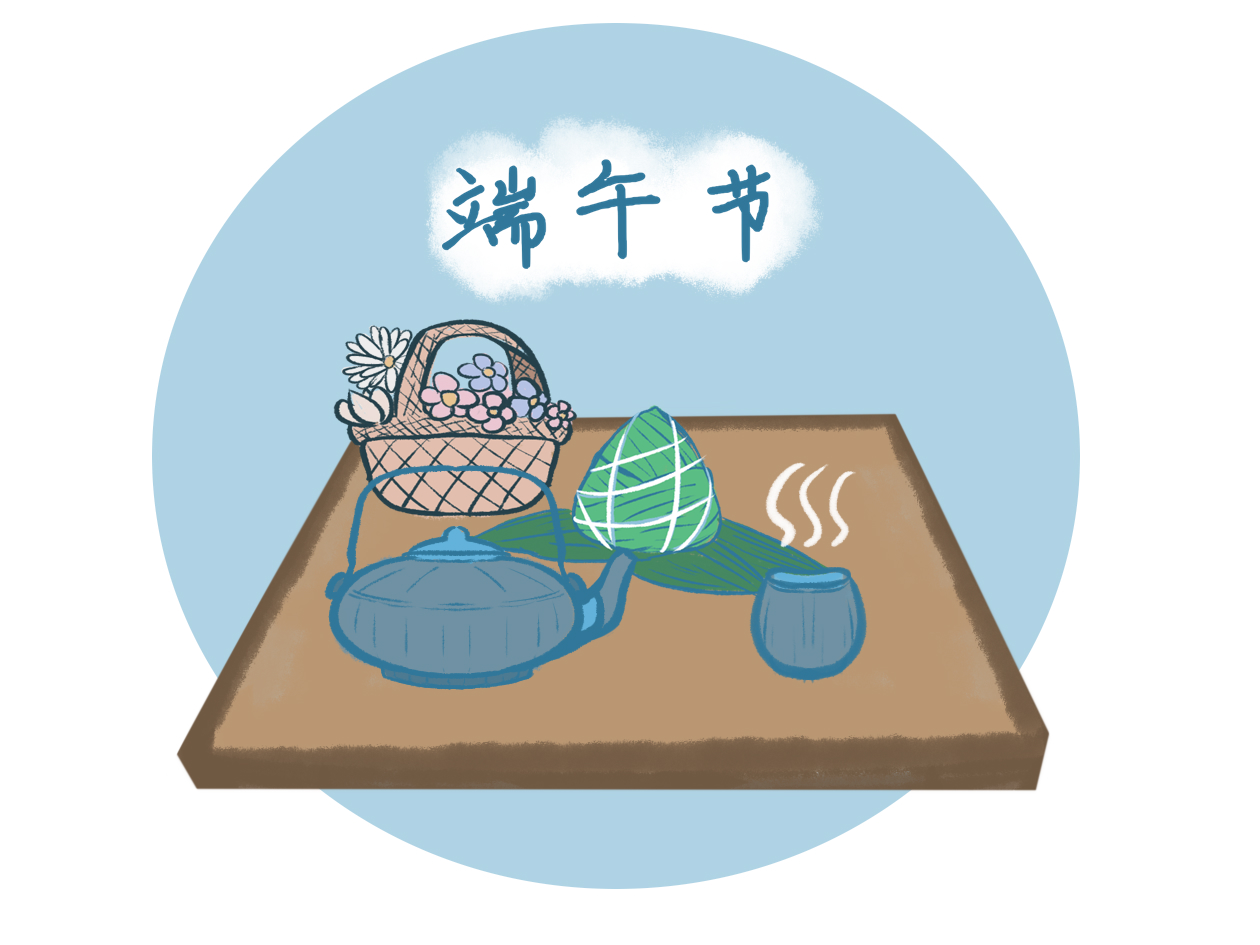写给青年的最初一封信
文丨朱光潜
朋友:
我写了许多信,还没有郑重其事地谈到人生问题,这是一则因为这个问题实在谈滥了,一则也因为我看这个问题并不如一般人看得那样重要。
在这最初一封信里我之所以提出这个滥题来讨论,并不是要说出什么一番大道理,不过把我本人平时几种对于人生的态度随便拿来做一次谈料。
我有两种看待人生的方法。在第一种方法里,我把我本人摆在前台,和世界一切人和物在一块玩把戏;在第二种方法里,我把我自己摆在后台,袖手看旁人在那儿装模作样。
站在前台时,我把我本人看得和旁人一样,不但和旁人一样,并且和鸟兽虫鱼诸物也都一样。
人类比其他物类痛苦,就因为人类把本人看得比其他物类重要。人类中有一部分人比其余的人苦痛,就因为这一部分人把本人比其余的人看得重要。
比方穿衣吃饭是多么简单的事,然而在这个世界里竟然成为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就因为有一部分人要亏人自肥。
再比方生死,这又是多么简单的事,无量数人和无量数物都已生过来死过去了。
一个小虫让车轮压死了,或者一朵鲜花让狂风吹落了,在虫和花本人都绝不值得计较或留恋,而在人类则生老病死以后偏要加上一个苦字。
这无非是因为人们希望造物主宰待他们本人应该比草木虫鱼特别优厚。
因为如此,我把本人看作草木虫鱼的侪辈,草木虫鱼在和风甘露中是那样活着,在炎暑寒冬中也还是那样活着。
像庄子所说,它们“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它们时而戾天跃渊,欣欣向荣,时而含葩敛翅,晏然蛰处,都顺着自然所赋予的那一副本性。
它们绝不计较生活应该是如何,绝不追查生活是为着什么,也绝不埋怨上天待它们特薄,把它们供人类分割凌虐。在它们说,生活本身就是方法,生活本身也就是目的。
从草木虫鱼的生活中,我收获了一个经验。我不在生活以外另求生活方法,不在生活以外另求生活目的。
世间少我一个,多我一个,或者我时而侥幸,时而受灾害侵逼,我以为这都无伤天地之和。
你如果问我,人们应该如何生活才好呢?
我说,就顺着自然所给的本性生活着,像草木虫鱼一样。
你如果问我,人们生活在这变幻无常的世相中究竟为着什么?
我说,生活就是为着生活,别无其他目的。你如果向我埋怨天公说,人生是多么苦恼呵!我说,人们生在这个世界并非是来享幸福的,所以那并不算奇怪。
这并不是一种颓废的人生观。你如果说我的话带有颓废的色彩,我请你在春天到百花齐放的园子里去,看看蝴蝶飞,听听鸟儿鸣。
然后再回到十字街头,细心瞧瞧人们的面孔,你看谁是活泼,谁是颓废?请你在冬天积雪凝寒的时候,看看雪压的松树,看着站在冰上的鸥和游在水中的鱼。
然后再回头看看遇苦便叫的那“万物之灵”,你以为谁比较能耐苦持恒呢?
我拿人比禽兽,有人也许视为异端邪说。其实我如果要征引“经典”,称道孔孟以辩护我的见解,也并不是难事。
孔子所谓“知命”,孟子所谓“尽性”,庄子所谓“齐物”,宋儒所谓“廓然大公,物来顺应”,和古希腊廊下派哲学,我都可以引申成一篇经义文,做我的护身符。
然而我觉得这大可不必。我虽不把本人比旁人看得重要,我也不把本人看得比旁人分外低能,如果我的理由是理由,就不用仗先圣先贤的声威。
以上是我站在前台对于人生的态度。但是我平时很欢喜站在后台看人生。
许多人把人生看作只要善恶分别的,所以他们的态度不是留恋,就是厌恶。
我站在后台时把人和物也一律看待,我看西施、嫫母、秦桧、岳飞也和我看八哥、鹦鹉、甘草、黄连一样。
我看匠人盖屋也和我看鸟鹊营巢、蚂蚁打洞一样,我看和平也和我看斗鸡一样,我看恋爱也和我看雄蜻蜓追雌蜻蜓一样。
因而,是非善恶对我都无意义,我只觉得对着这些纷纭扰攘的人和物,好比看图画,好比看小说,件件都很风趣味。
这些风趣味的人和物之中自然也有一个分别。
有些风趣味,是因为它们带有很浓厚的喜剧成分。有些风趣味,是因为它们带有很深刻的悲剧成分。
我有时看到人生的喜剧。前天遇见一个小外交官,他的上下巴都光光如也,和人说话时却常常用大拇指和食指在腮旁捻一捻,像有胡须似的。
他们说这是官气,我看到这种举动比看诙谐画还更风趣味。许多年前一位同事常常很气愤地向人说:“如果我是一个女子,我至多已接得一尺厚的求婚书了!”
偏偏他不是女子,这已经是喜剧;何况他又麻又丑,纵然他幸而为女子,也绝不会有求婚书的麻烦,而他却以此自鸣得意,这总算得喜剧之喜剧了。
这件事和英国文学家哥尔德斯密斯的一段逸事一样风趣。
他有一次陪几个女子在荷兰某一个桥上散步,看见桥上行人个个都留意他同行的女子,而没有一个睬他本人,便板起面孔很气愤地说:“哼,在别的地方也有人这样看我咧!”
如此等类的事,我天天都见得着。在闲静寂寞的时候,我把这一类的小小事件从记忆中召回来,寻思玩味,觉得比抽烟饮茶还更有味。
老实说,假如这个世界中没有曹雪芹所描写的刘姥姥,没有吴敬梓所描写的严贡生,没有莫里哀所描写的达尔杜弗和阿尔巴贡,生命更不值得留恋了。
我感激刘姥姥、严贡生一流人物,更甚于我感激钱塘的潮和匡庐的瀑。
其次,人生的悲剧尤其能使我惊心动魄;许多人因为人生多悲剧而悲观厌世,我却以为人生有价值正因其有悲剧。我在几年前做的《无言之美》里曾说明这个道理,现在引一段来:
我们所居的世界是最完满的,就因为它是最不完满的。这话表面看来,不通已极。但是实含有至理。
假如世界是完满的,人类所过的生活——比好一点,是神仙的生活;比坏一点,就是猪的生活——便呆板单调已极,因为倘若件件事都尽美尽善了,自然没有希望发生,更没有努力奋斗的必要。
人生最可乐的就是活动所生的感觉,就是奋斗成功而得的快慰。世界既完满,我们如何能尝创形成功的快慰?
这个世界之所以美满,就在有缺陷,就在有希望的机会,有想象的田地。换句话说,世界有缺陷,可能性才大。
这个道理李石岑先生在《一般》第三卷第三号所发表的《缺陷论》里也说得很透辟。
悲剧也就是人生一种缺陷。它好比洪涛巨浪,令人在平凡中见出庄严,在黑暗中见出光彩。
假如荆轲真正刺中秦始皇,林黛玉真正嫁了贾宝玉,也不过闹个平凡收场,哪得叫千载以后的人唏嘘赞赏?
以李太白那样天才,偏要和江淹戏弄笔墨,做了一篇《反恨赋》,和《上韩荆州书》一样庸俗无味。
毛声山评《琵琶记》,说他有意要做“补天石”传奇十种,把古今几件悲剧都改个快活收场,他没有实行,总算是一件幸事。
人生本来要有悲剧才能算人生,你偏想把它一笔勾销,不说你勾销不去,就是勾销去了,人生反更索然寡趣。
所以我无论站在前台或站在后台时,对于失败,对于罪孽,对于殃咎,都是一副冷眼看待,都是用一个热心惊赞。
朋友,我感激你费去宝贵的时光读我的这十二封信,如果你不厌倦,将来我也许常常和你通信闲谈,现在让我暂时告别吧!
你的朋友 孟实
来源:文章选自作者《好的人生,不焦急: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作者简介:
朱光潜(1897年9月19日—1986年3月6日),笔名孟实,安徽省安庆市桐城县人。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历任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教授。朱光潜终身努力于美学研究,美学教学,开创了中国美学研究的新领域。次要著作有《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西方美学史》《谈美》等。
↓↓为您推荐↓↓
上一篇:隋唐冷知识——隋唐时期的数学成就
下一篇: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