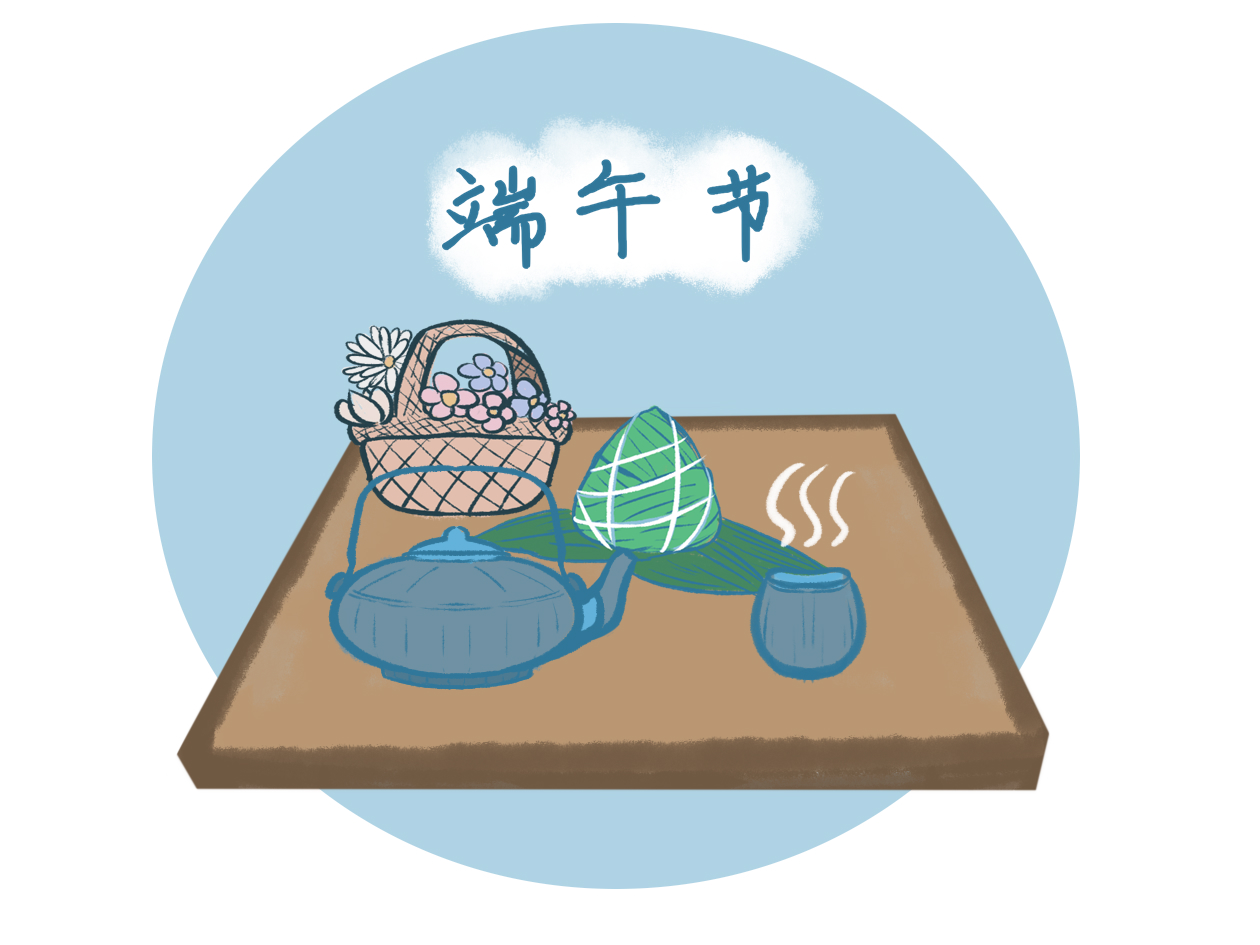苟生是我的远房亲戚,和我年纪不相上下。小时候去外婆家,就能见到他。那个时候不明白他为什么有一个如此不雅的名字。后来听外婆讲,苟生他妈怀上他就多病,生怕苟生也一样,请人起了这个名,图他好养活。
苟生小学还没上完,就跟我外公学做篾匠了 —— 我外公编织箩筐是把好手。逢赶圩日,作为徒弟的苟生挑着叠起的两挑子箩筐,走得飞快,外公两只手靠在后背,一点也不急。外公自然是不急的,因为他的货抢手,每每一到镇上,就遇到了买家。
外公的箩筐年年都是一个价,我记得从我读小学开始,直到高中毕业,价格还是八块钱一挑。这等收益的手艺,苟生早就撂挑子不干了,去了广东。
每年正月,我都遵父母命上外婆家拜年。苟生家正月里一定要请他师傅吃饭的,此时也请上我。因出门时父母有交代,除了外婆家哪里都不能去,所以我呢,就躲进房间里。苟生没请动我是决不罢休的,他那双习惯破了毛竹和篾丝的手,粗糙且粗暴,像铁爪一样,紧紧的钳住了我的手臂,任由他拖拽着我,不断到他家里,才松开。
自然是满满一桌子的菜,和温的发烫的酒,热气腾腾的。
后来去外婆家,见到了从广东回家过春节的苟生,他的头发卷卷的,且染了好几样色,上下紧身的衣裳,闪着光,嗓门也粗了很多,一颠一颠地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像漂亮的公鸡。原来他南下广东时学了一阵子理发,不久就本人开了一家理发店,生意好好的。
后来,外婆外公先后去世。再后来,听闻苟生也死了,说是他谈了一个外地的女朋友,是他店里的洗头工,两个人好得紧,相约去附近的铁轨上拍定情照,也许是太投入了,浪漫地断送在了疾驰而来的列车下。
苟生这个贱名,保佑不了贱民的一辈子。过了这么多年,我仍然不能停止对他的感伤,与其说是为了他的不幸,不如说是为本人的宿命。
下一篇: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