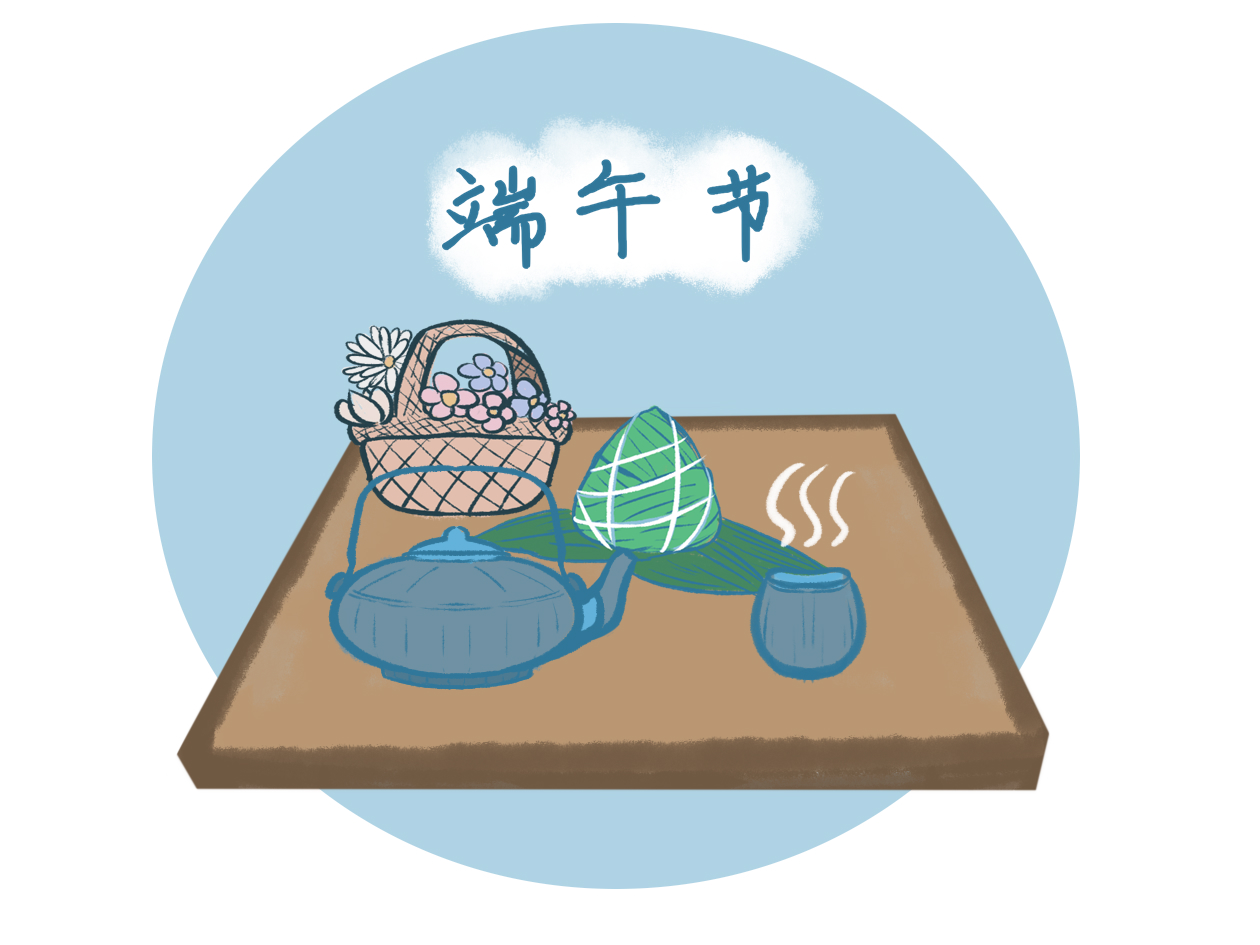漩涡
一
太阳落山,伊格拿特才从镇里回来。
他推开树枝编的栅门,推倒一个尖顶的雪堆,把霜花满身的马拉到院子里,也不卸套就跑上台阶。只听见门廊里结冰的地板吱格吱格发响,接着,扫帚匆匆地扫着毡靴上的雪,发出苏苏的声音。巴霍梅奇在炕上削斧柄,听见大儿子回来,就拂去膝盖上的刨花,对小儿子格利戈里说:
“你去卸马,干草我已经堆在马房里了。”
门大大地打开了,伊格拿特低着头走进来,问了好,好一阵用冻僵的手指解着风帽。他皱着眉头,把胡子上半溶解的冰凌子拉掉,但不掩饰内心的快乐,笑了笑说:
“听到一个消息——红卫军开过来了……”
巴霍梅奇从炕上挂下腿,假装镇静地问:
“是打过来还是怎样的?”
“有各种说法……只是镇里人心惶惶,老百姓都很激动,镇公所里挤得人山人海的。”
“关于土地你没听到什么消息吗?”
“有人说,布尔什维克要把地主的地统统没收了。”
“噢——噢!”巴霍梅奇叫出声来,生气勃勃地从炕上跳下来。
老伴在火缸边搅动匙子,把药汤盛到盘子里,说:
“叫格利戈里来吃晚饭。”
天色晚了。雪时下时停,夜张开青灰色的帷幕。巴霍梅奇放下匙子,用绣花的手巾擦擦胡子问:
“关于汽磨打听到什么消息没有?什么时候开工啊?”
“磨坊已经开工,可以运去磨了。”
“嗯,快吃完饭,我们到仓里去。谷子得再簸一次,明天要是天好,我一早就运去磨。路怎样样,没有坏吧?”
“路没有封住,白天黑夜都有车马来往,只是两辆车子对面行驶有点困难。路两边的雪比腰还深呢。”
二
格利戈里把父亲送到门外。
巴霍梅奇拉上手套,坐到雪橇的前座上。
“格利戈里,你得留神那母牛。它的奶头发胀,眼看着就要生产了……”
“好的,爸爸,你去吧!”
雪橇的滑板飒飒地刨着微融的积雪。巴霍梅奇抖动毛缰绳,绕过街上一堆堆的炉灰。碰到没有雪的地面,雪橇的切口就常常冰住。几匹马拉长身体,费劲地拖着雪橇。虽然马具很好,马也吃得饱饱的,可是巴霍梅奇还是不时跳下雪橇来,还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刚才装那些袋子,实在把他累坏了。
上了山,他让汗淋淋的马歇了一会儿,又催动它们跑起快步来。在向阳的地方,积雪开始融解,道路就变得高低不平了。早春的天气暖和得出奇。半夜时分,冰也开始融解了。
巴霍梅奇刚开始绕树林行进,迎面跑来一辆三驾雪橇。树林旁边的雪积得像山一样高。在那些六七尺宽的雪堆两头,来往的车马压出一条狭窄的小路。在这种小路上,对面来的两辆橇子是无法错过的。
“哎,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事!……得噜!……”
巴霍梅奇止住马,跳下雪橇,摘下帽子。风NFDA9着他那汗光光的灰白脑袋。巴霍梅奇所以摘下头上破旧的帽子,因为认出三驾雪橇上坐着契尔诺亚罗夫上校。而他租用上校的土地,整整有八年了。
三驾雪橇越来越近了。铃铛在互相低语。看得见,旁边的两匹马汗沫飞溅,两头的一匹马拼命飞跑。车夫站起来,挥动鞭子。
“让开,老乌鸦!……干什么把路挡住啦?……”
跑近了,车夫才勒住马。巴霍梅奇跌跌跄跄地绊着大衣的前襟,光着脑袋向雪橇跑去,低低地鞠了一躬。
在铺着熊皮的雪橇上,一双眼睛弹了出来,一眨不眨地望着。两片刮得发青的薄嘴唇扭歪了。
“哼,庄稼佬,你干什么不让路?学会布尔什维克的自在了吗?也要讲讲平等吗?……”
让我吧。您是空橇,我是装满货的……我要是一离开道路,就再也拔不出来了。”
尊崇军官的肩章,让路!……”
他抖落腿上的毯子,把一只羊皮手套扔在车座上。
“阿尔焦姆,拿鞭子来!”
契尔诺亚罗夫上校从雪橇上跳下来,挥了挥鞭子,就“啪”的一下抽在巴霍梅奇的两眼两头。
老头儿喔唷一声,身子摇晃了一下,两手扪住面孔,血就从手指缝里流出来。
“哼,给你尝尝味道,坏蛋!……”
上校一把拉住巴霍梅奇的灰白胡子,哑着嗓子,唾沫四溅地说:
“我要打掉你们的红卫军思想!……庄稼佬,记住我契尔诺亚罗夫上校!……记住!……”
蓝色的车轭突起在微融的雪地上。铃铛隐隐约约地低语着……在道路旁边,巴霍梅奇的两匹马在挣扎,想挣断套绳;翻倒的雪橇无可奈何地横在地上,辕木折断了。巴霍梅奇茫然地目送着三驾雪橇,直到像天鹅脖子一样弯曲的雪橇的后部消失在峡谷里。
巴霍梅奇死也不会忘记契尔诺亚罗夫上校的。
三
巴霍梅奇的老伴挑着水桶,从水井那儿走来。
白嘴鸦在光秃秃的柳树丛里聒噪。太阳落到村外小岗上红屋顶磨坊的风车叶子板两头了。水在渠道里汩汩地流,流得篱笆都摇晃不停。天空好像一朵蔫了的樱红色的花。
她走近院子,看见门口停着一辆马车,有两匹驿马,卷着短短的尾巴。在马的溅满泥浆的冻僵的腿旁,几只母鸡正趴着热气腾腾的马粪。一个戴黑羔皮帽的瘦长男人,撩起军大衣前襟,从车上下来。他那张冻僵的面孔向老太婆转了过来。
“米哈依尔!……好儿子!……真没想到!……”
她抛下扁担和水桶,抱住儿子的脖子,干瘪的嘴唇却够不到儿子的嘴唇,脑袋撞着儿子的胸膛,又吻着他那闪亮的钮扣和灰色的呢军服。
母亲的破短袄发出牛粪的气味。他悄悄地往后一闪,笑了笑,嫌恶地对母亲说:
“街上不方便,妈妈……您说,马应该安顿到哪儿去?还有,您把我的手提箱拿到屋子里去吧……车夫,赶到院子里去,听见吗?”
四
少尉。簇新的肩章。生着稀疏的短头发的脑袋。是本人的儿子,本人的骨肉,可是巴霍梅奇像看见陌生人一样害臊。
“好儿子,你回来可以待一阵吗?”
“我是从诺伏契尔卡斯克出差来的,负有军长交托的特别任务。我大概要待……妈妈!把桌上的牛奶擦掉,怎样这样脏……我大概要在这儿待两个月。”
伊格拿特从院子里走来,肮脏的靴子在地上留着脚印。
“啊,弟弟,你好!……来得太好了。”
“你好。”
伊格拿特伸出手,想去拥抱弟弟,不知怎的没有抱成,只冷冷地互相握了握手指。
伊格拿特勉强笑着说:
“弟弟,你还戴肩章,我们可早就扔掉了……”
米哈依尔皱起眉头。
“我还没有把哥萨克的荣誉出卖掉。”
大家沉闷地不作声。
“你们的日子过得怎样样?”米哈依尔一面问,一面俯下身去脱靴子。
巴霍梅奇从长凳上站起来,冲到儿子跟前。
“让我来给你脱,米哈依尔,别把你的手弄脏了。”巴霍梅奇跪下来,一面小心地给儿子脱靴子,一面回答说,“过日子,吃麦子。我们的生活你是晓得的。你们城里有什么消息吗?”
“我们在组织哥萨克去打退红卫军。”
伊格拿特眼睛瞪着泥地问:
“为什么要去打退他们呢?”
米哈依尔冷笑了一下说:
“你不晓得吗?布尔什维克要取消我们的哥萨克身份,还想搞公社,把一切都收归公有——土地也好,婆娘也好……”
“胡说八道!……布尔什维克在推行我们的路线。”
“什么是你们的路线?”
“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人民,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伊格拿特,你怎样,反对布尔什维克吗?”
“那你反对谁呢?”
米哈依尔不作声。他坐着,向流满水气的窗子转过身去,接着笑嘻嘻地用手指在玻璃上划着模糊的花纹。
五
在小谷后面,在幼橡树树梢后面,一座坟山隆起在盖特曼大道旁边。
坟山上有一座年久剥落、孔洞累累的石头女像,石像的头部长满野草。每天晚上,太阳越过石像,慢慢地向上爬。粘腻而暖热的阳光,穿过雾沉沉的尘幕,像母狗舔小狗似的舔着草原、花园和房子的瓦屋顶。
巴霍梅奇大清早就带着犁,离开大道。他用老年人的蹒跚的步伐量出四公顷地,向两头红褐色的公牛抽了一鞭子,就开始用犁划破黑土。
格利戈里用力压住犁梢,把土翻得差不多齐膝盖高,巴霍梅奇却在光滑的犁沟里一瘸一瘸地走着,挥动鞭子,欣赏着儿子:别看他只要十八岁,干起活来可比随便哪个哥萨克都强。
他们赶了三个趟儿停住了。太阳升起来了。陷在土里的石头女像,用无形的眼睛从坟山上望着耕地的人们。她的身体被太阳光照得通红,好像被火焰包围着一样。风把大路上极细的灰尘吹成一条动荡的柱子。格利戈里定睛一看——有个人骑马跑来。
“爸爸,是不是我们的米哈依尔骑马跑来了?”
“好像是他……”
米哈依尔跑近了,把汗淋淋的马弃在营帐旁,跌跌跄跄地向耕地的人们跑来。跑近了,气急得喘不过来,好像一匹赶坏了的马。
“你们在耕谁的地?!”
“我们的地。”
“这地不是属于契尔诺亚罗夫上校的吗?”
巴霍梅奇擤了擤鼻涕,拿粗布衬衫的下摆擦擦鼻子,缓慢而无力地说:
“从前是他们的,可现在呀,儿子,是我们的了,是人民的了……”
米哈依尔脸色惨白,嚷道:
“爸爸!我晓得这是谁干的事!……格利戈里和伊格拿特会让你倒霉的!……抢别人的东西,你得担任。”
巴霍梅奇倔强地低下头说:
“现在是我们的土地!……现在可没有那样的法律,让什么人拥有一千公顷以上的土地……不行!大家一律平等……”
“你没有权利耕别人的地!……”
“他也没有权利占有整个草原。我们在盐土上播种,可他占有黑土,他那片地荒了三年了。天下有这种道理吗?……”
“别讲了,爸爸,不然我会命令村长把你逮捕的!……”
巴霍梅奇猛地转过身去,脸涨得通红,痉挛地抽动脑袋,嚷道:
“我用我的血汗钱培养你……让你受教育!……你这个坏蛋,畜生!……”
米哈依尔脸色发青,牙齿咬得格格响:
“我要给你这老东西……”他握紧拳头,向父亲迈近一步,可是一看见格利戈里抓起一根铁棍,穿过耕地,连跳带蹦地跑来,就把脑袋缩在肩膀里,头也不回地跑回村子里去了。
六
巴霍梅奇有一座小泥房。庭院四周的栅栏,一根根地竖立着,好像马的肋骨一样。
格利戈里跟父亲一起从地里回来。伊格拿特在用树枝编牲口院子的围栅,看见他们回来,就迎了上去。他的手里发散着烂叶子的刺鼻的气味。
“格利戈里,村公所要我们去。广场上在召集村民大会。”
“干什么呀?”
“听说要动员了……红卫军占领卡林诺夫村了。”
晚霞在打谷场围栅后面暗淡下去,快要消灭了。在打谷场的棕黄色的糠堆上,留下一条残阳。东风吹着糠堆,接着太阳的余辉也消失了。
格利戈里洗净马,上了饲料。鳏居的伊格拿特侧着身子,正在台阶上张罗六岁的儿子。格利戈里走过,瞧了瞧哥哥的笑得细细的眼睛,喃喃地说:
“夜里得跑到卡林诺夫去,留在这儿会被动员去的!……”
母亲从门廊里赶着小牛出来,格利戈里就对她说:
“妈妈,你把我和伊格拿特的衬衣拿出来,再装一袋面包干……”
“活见鬼,你们这是要上哪儿去啦?……”
“走到哪儿是哪儿。”
村里的广场上人声沸腾,直到深夜。巴霍梅奇从那儿回来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他在格利戈里睡觉的仓房门口站住了。站了一会儿,寂然地在石头门槛上坐下来。他感到一阵窒闷,心扑扑地跳得很重,耳朵里鸣响着尖锐而拖长的声音。他坐着,向倒映着淡淡的月亮的结冰的水洼子唾了一口口水,心里痛苦地意识到,过惯了的平静生活一去不返了。
几条狗在顿河附近的菜园子那儿汪汪乱叫,一只鹌鹑在草地上匀调而嘹亮地鸣啭。夜幕张开在草原的上空,白雾笼罩着农家的院子。巴霍梅奇干咳了几声,嘎的一下推开门。
“你睡着啦,格利戈里?”
仓房里一片寂静,只闻到堆藏着的谷物的味儿。他走进去,摸到羊皮大衣。
“格利戈里,睡着了吗?”
“不,没有。”
老头儿在大衣边上坐下了,格利戈里听见父亲的手在轻轻哆嗦。巴霍梅奇低沉地说:
“我要跟你们一块儿去……到布尔什维克那儿……去服务……”
“真的吗,爸爸?……那么家里怎样办呢?你年纪又大……”
“怎样,你说我老吗?我可以参加辎重队,要是办不到,骑马也行……家里让米哈依尔去管得了……他不是我们的人,土地也不是我们的……让他去过活吧,上帝会裁判他的,我们要去夺回供养我们的土地!”
第一批公鸡参参差差地啼起来。在顿河上空,在顶梢参差的树林后面,朝霞燃烧起来。阴影悄然地溜走了。
巴霍梅奇拉出三匹马,饮了水,小心地抚平马衣,加上鞍子。打谷场的门吱嘎一声,像陪着巴霍梅奇的老伴一起呜咽,马蹄在盐土上“嗒嗒”地响起来。
“爸爸,我们得走夏季路,走大路会被他们拦住的!”伊格拿特压低嗓子说。
天亮了。草上滚动着带蜜香的冰冷的露珠。朝晨从顿河对岸,从柠檬黄的细砂滩上,迈着大步来临了。
七
在契尔诺亚罗夫上校的灰绿色军服上,有九颗星是用紫铅笔画上去的。胖胖的面颊透显露一条条青色的脉管。发音不清的贵族式男中音,撞在广场上结满蛛网的墙上。保养得很好的白里透红的胖手指,潇洒地做着手势。
四周挤满浑身是汗的人们,热辣辣地吐出熏人的土烟草和酸溜溜的小麦面包的气味。红顶的皮帽子,各色的大胡子。全都张着嘴巴,流着口涎,出神地听着。发音不清的讨厌的男中音,从花柳病烂坏的嘴唇里发出来:
“亲害(爱)的村民们!……你们总(从)古以来就害(爱)护沙光(皇)爸爸和土(祖)国。现才(在),才(在)这个伟大的混乱的时代,整个奥(俄)罗斯都才(在)望着你们……布尔什维克侮辱土(祖)国,你们快来救土(祖)国!……救救本人的财产,本人的老婆和玉(女)儿……你们的同乡米哈依尔少尉,就是开(克)尽公民责任的最好榜样:他休(首)先来向我们报告,他的父亲和两个兄弟跑到布尔什维克那边去了。他第一个出来保卫静静的顿河,他是顿河的正(真)正的儿子!……”
告示
本村哥萨克巴霍梅奇率子伊格拿特及格利戈里,背叛静静的顿河,投奔敌方,特公告剥夺其哥萨克称号,并没收其全部份地及公地上之权利,如有人捕得该犯父子,着即送维申斯克村战地法庭,此告。
八
队伍在去年堆的干草垛旁边停下来喂马。一挺机枪在村外打谷场后面哒哒地响着。
单面面颊被打穿的政委,骑着一匹汗泡满身的公马,跑到机枪车旁边,用带鼻音的嘶裂的嗓子嚷道:
“没有希望啦!……瞧着吧,我们要挨打了!……”
他照公马的耳朵两头抽了一鞭子,喉咙被黑色的血痰卡住了,声嘶力竭地对住队长的耳朵说:
“我们不能突破到顿河边上,就完蛋了!哥萨克会把我们杀死,把我们捣成肉酱的……快召集大家,实行进攻……”
队长原来是铸铁厂的机工,动作像飞轮起步一样慢,抬起剃得光光的脑袋,并不拉出嘴里的烟斗,命令道:
“上马!……”
政委骑马跑了两丈路,回头问:
“你想我们会被消灭吗?……”接着不等回答,又向前跑去了。
子弹把面粉一样细的灰尘,从马蹄下扬起来,又飒飒地钻进干草里。一颗子弹削下机枪车上的一条木片,打中了机枪手。机枪手丢掉手里涂柏油的包脚布,坐下来,像鸟儿一样低下头,披散头发,就这么死了——一只脚穿着靴子,一只脚没有穿。风从铁路路基上送来机车的颤抖的隆隆声。在装甲车的车皮上,一个出套的短筒炮口,转过来对着草原,向干草堆,向骚乱的人群开了一炮。接着,链条“哗NFDACNFDAC”地响着,装甲列车“科尔尼洛夫八号”重又开动了。射出来的炮弹落在干草堆的左边。列车隆隆地响着,放出一股柏油一样黑的浓烟,冲掉轨道上去年留下的错综的西瓜藤。
生锈的铁轨在过度的重压下呜咽了好一阵,枕木发出格勒勒的响声;可是,在干草堆旁边的草原上,巴霍梅奇的怀孕的马,腿上中了榴弹,好一阵挣扎着要站起来:它抬起头,喷着鼻子,脚上磨坏的蹄铁闪闪发亮。砂岩贪婪地吸着淡红的口沫和深红的群血。
巴霍梅奇的心痛得变硬了,他喃喃地说:
“一匹纯种的母马呐……唉,早知这样,不该带来的!……”
“别想不开了,爸爸!……”伊格拿特在飞跑的马上嚷。“快坐到马车上去,没看见马上要进攻了!……”
老头儿在他后面茫然地瞧了一眼。
机枪的发射声,好像撕碎粗布的声音。巴霍梅奇躺在子弹箱上,吐着苦涩的口水。大地饱经春雨、太阳、带薄荷和苦艾味的草原风的折磨,像流动的烟雾似的分发出焦黄的泥土气,和根部腐烂的隔年野草的使人感到酥痒的香气。
凹凸不平的蓝色的树林边缘,在地平线上震动。穿过洋溢在草原上空的黄澄澄的灰砂,一只云雀发出一串珍珠般的颤音,响应着机枪的射击声。格利戈里骑马去取子弹。
“爸爸,不要伤心。一匹母马算不了什么!……”
格利戈里的褐色嘴唇热得龟裂了,眼皮因为夜里失眠而浮肿起来。
他一下子抱起两箱子弹,抖动蓬乱的头发,脸上满是汗水,但是浮着浅笑。
傍晚他们来到了顿河边上。直到天黑,炮兵连从谷地里开着炮,哥萨克的骑兵侦查队直立在小岗上。夜里,探照灯的大胆的黄眼睛,向荆棘丛里乱射,探索着拴马桩和营帐。它执着地照了有一分钟的样子,倾泻出死气沉沉的光芒,又熄灭了。
天蒙蒙亮,队伍从山岗上下来,一个跟着一个,好像波浪,又像一串链子。从乱蓬蓬的荆棘丛里,枪弹沉着精确地一梭子一梭子发射着。半夜,队长在补过的靴子底上敲出烟斗里的灰,用冷淡而沉重的眼光向大家扫了一下:
“情况糟得很,同志们!……大家游过河去吧,再走二十里就是格罗莫夫村,”他没精打彩地结束说,“那边有我们的人……”
格利戈里解下马鞍,对父亲嚷道:
“你怎样啦?!”
“胡闹!……”巴霍梅奇严厉地说,可是他的下巴骨哆嗦起来了。“你游过去吧,格利戈里!……把马嚼子去掉……我可不行了……老了……”
“别了,爸爸!……”
“上帝保佑你,孩子!……”
“喂,秃马,走!走,他妈的,害怕啦!……”
格利戈里身体浸到水里,直到腰部,直到胸部,最初,只要他那皱紧眉头的脑袋和马的警惕的耳朵,突出在青灰色的水面上。
巴霍梅奇用一只压扁的手指把弹夹推进膛里,在准星上捕捉着跑来跑去的人们,随后扔掉最初一颗冒烟的弹壳,举起毛茸茸的两手说:
“伊格拿特,我们完啦!……”
伊格拿特对住马的嘴脸开了一枪,坐下来,叉开两腿,向一块湿的被波浪吻得光溜溜的石卵子唾了一口,抓住草绿色衬衫的领子,哗啦啦地不断撕到腰部。
九
吃早饭的时候,米哈依尔得意洋洋地撚弄着搽过油的淡黄色小胡子。
“妈妈,现在把我提升为骑兵中尉了,因为我把布尔什维主义连根拔掉了。我是不好惹的,稍微有点什么就枪毙!”
母亲叹了一口气:
“米哈依尔,你说,爸爸他们怎样了?……也许会回来吧……”
“妈妈,我是个军官,又是静静的顿河的忠实儿子,可不能考虑什么亲属关系。不论父亲,不论亲兄弟,一律送交法办……”
“好儿子!……我的米哈依尔!……叫我怎样办呢?……你们都是我的奶喂大的,我都一样疼!……”
“不能有丝毫同情心!……”他严厉地扫了一眼伊格拿特的儿子:“把这个小畜生从桌子边拉走,不然我会扭断他的脖子的,共产小杂种!……你瞧,他看人的样子,活像一头小狼……将来长大了,也是个布尔什维克,像他父亲一样,小坏蛋!……”
十
顿河附近的菜园子,分发出春潮和白杨嫩芽的味儿。梳子般的波浪,摇荡着河里的野鹅,冲击着菜园子的篱笆。
巴霍梅奇的老伴在种马铃薯,费劲地在一个个小槽间转动。她弯下腰,血涌到脑袋,感到头昏眼花。站了一会儿,坐下来,默默地瞧着手上错综凸起的青筋。凹陷的嘴唇无声地嘟哝着。
伊格拿特的儿子在篱笆外的砂地上玩耍。
“奶奶!”
“什么呀,小孙子?”
“快来看,奶奶,河水漂来什么东西啦。”
“漂来什么呀,宝贝?”
老太婆站起来,不慌不忙地把铲子插在地上,吱嘎一声推开门。浅滩上横着一匹死马,腿贴住地面,身上的水闪闪发亮,肚子斜斜地裂开了。风吹来一阵阵的尸臭。
老太婆走过去。
一个人双手死抱住马脖子,左手上紧紧地绕着缰绳,头向后仰,头发挂在眼睛上。老太婆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看见被鱼咬坏的嘴唇显露牙齿笑起来,就扑了下去……
她摇动灰白的头发,向水里爬过去,一把抱住乌黑的脑袋,叫道:“格利戈里!……小——儿——子!……”
第186号命令(抄本)
北线司令:
骑兵中尉米哈依尔在上顿河区清剿布尔什维主义,英勇忘我,特晋升为骑兵上尉并任命为某战地法庭警卫队长,此令。
少将伊凡诺夫
参谋(字迹不清)
十一
一条被烽火烧焦的道路。几个兵骑在马上押着他们两人在路上走。脚底都溃烂了。身上只穿一套衬衫裤,被血水渗透了。他们在枪林弹雨下走过一个个村庄、一条条挤满人的街道。走了一天一夜,第二天黄昏来到故乡。顿河,还有那一排青灰色的白垩山,仿佛一群绵羊。巴霍梅奇弯下腰,拔了一把绿色的小麦,困难地移动嘴唇:
“认得吗,伊格拿特?……这是我们的地……是跟格利戈里一起耕的……”
盘绕着的鞭子在后面呼啸了一声。
“不许说话!……”
他们垂下头,在村子里默默地走着。脚变得像铅一样重。他们经过栅栏,经过泥房子。巴霍梅奇望了一眼野草丛生的庭院,摩摩胸部,觉得心像针刺一样痛。
“爸爸!你瞧,妈妈在打谷场里……”
“她没有看见!……”
后面发出了叫声:
“闭嘴,王八蛋!……”
长满杂草的广场。乡公所。台阶旁边集合了好多人。
“好啊,巴霍梅奇!……是不是去争土地来着?”
“他已经在坟地上争到六尺地了。”
“给他这条老狗也来一个教训!”
巴霍梅奇举起一只指甲浮起的手指,痉挛地喘着气,好容易说:
“呸,去你妈的……虽然我们活不成了,虽然我们完蛋了,可是你们……人家不会忘记的。真理不在你们的一边!”
邻居马凯耶夫侧身走到巴霍梅奇跟前,抡开手臂,从褐色的大胡子里显露牙齿,一言不发地向巴霍梅奇的头部打去。
“打呀!!!”后面有人叫道。
人群像浪潮一样带着野兽般的吼声涌过来,晃动红顶皮帽子,在疯狂的混乱中聚拢来。在急促的脚步声中,拳头发出黏滞而响亮的声音……米基沙拉忽然像鸢一样从台阶上窜下来,两手分开汹涌的人群。他穿着撕破的衬衫,冲过去,脸色发白,嘴巴扭歪,大声嚷道:
“弟兄们!……战士们!……不许打死他!……”他从鞘里抽出刀,寒光闪闪地在头上划了个扇子形。“上前线谁也不肯去,他妈的……现在倒会杀人啦?!”
“打米基沙拉!……他投降布尔什维克啦!……”
人们像一堵厚厚的墙,把米基沙拉包围起来。八个从前线回来休假的兵士,把巴霍梅奇和伊格拿特跟人群隔离开来。
老人们站了一会儿,喧闹了一阵,三三两两地从广场上走散了。天色黑了……
“很想听听您的最初决定,上尉。当然啰,应该把他们枪毙,可是不论怎样说,到底是您的父亲和哥哥……也许,您为他们到军法处长那儿去求求情吧?……”契尔诺亚罗夫上校口齿不清地说。
“大人,我用决心和真理为沙皇、为伟大的顿河军队效过忠,以后将继续效忠……”
上校做了一个怜悯的手势说:
“上尉,您的灵魂是高尚的,您的心是刚强的。为了您在效忠沙皇陛下和祖国人民上的忘我精神,让我照俄罗斯规矩来吻吻您吧!……”
啧啧啧地接了三次响吻,然后沉默了一阵。
“您认为怎样样,亲爱的上尉,要是把他们枪毙了,会不会引起最穷的哥萨克的愤怒?”
米哈依尔上尉沉默了好一阵,然后,没有抬起头来,声音低沉地说:
“押送队里有可靠的小伙子……可以叫他们押到诺伏契尔卡斯的监狱里去……他们不会泄露的……可是犯人有时候会逃跑……”
“我了解您,上尉!……您有希望升为大尉。让我来握握您的手!……”
十二
拘留战俘的仓房,四四周着带刺的铁丝网,好像蛛网一样。铁丝网后面站着伊格拿特和巴霍梅奇,面孔浮肿,面色黑得像铁;街上站着伊格拿特的儿子,头上戴着父亲的帽子,巴霍梅奇的老伴用生硬的双手抓住铁丝网。她NFDA2动血污的眼皮,歪着嘴巴,可是没有眼泪——眼泪都哭干了。
巴霍梅奇困难地转动破裂的舌头说:
“小麦请鲁基奇来割吧,可得酬劳他,送他一头周岁的小牛。”
接着咬咬嘴唇,干咳了几声又说:
“老太婆,不必为我们伤心!……活够了……早晚总得到那边去的。将来给我们做个丧事礼拜。得记住,不能写:‘红卫军巴霍梅奇’,只能写:‘阵亡军人巴霍梅奇、伊格拿特、格利戈里’……不然神父不肯接受的……嗯,别了,老太婆!……活下去……要爱护孙子。如果我什么时候得罪过你,那就请你原谅……”
伊格拿特两手抱起儿子。哨兵别转身去,假装没看见。伊格拿特手指哆嗦,用芦苇给儿子做风车。
“好爸爸,你头上怎样有血啊?”
“我这是碰伤的,乖儿子。”
“你刚才从仓房里出来,那个叔叔干什么用枪打你啊?”
“你这孩子真怪!……他这是打着玩的,开玩笑……”
大家沉默着。芦苇在伊格拿特的指甲下飒飒地响。
“我们回家去吧,好爸爸?风车你到家里去给我做好了。”
“你跟奶奶先走吧,乖儿子……”伊格拿特的嘴唇伤心地抖动了一下,扭歪了。“我过会儿就来……”
伊格拿特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好像一头系着的狼。他拖动被枪柄打伤的腿,走到瘦弱的小牛跟前,紧紧地把它抱在胸前。
“好爸爸,你的眼睛怎样湿啦?”
伊格拿特不作声。
黄昏的微光熄灭了。从草地上,从河滨的灌木丛里,从赤杨林和沼地上,雾气飘到花园里,变成雪白色的露珠,把青草压倒在又冷又湿的地上。
仓房里出来几个人。一个佩上尉肩章的瘦长军官,头戴黑羔皮帽子,嘴里喷着土烧酒的气味,压低嗓子悄然地说:
“不用带到远处去!……村外的小树林里就行了!……”
在寂静的夜里传出重重的脚步声和步枪枪闩的喀嚓声。
这是一个没有星星、狼嚎不止的黑夜。顿河对岸的青灰色草原变得模糊不清了。在小山上——在麦苗茂盛的田野后面,在被春潮冲洗过的谷地里,在一片被暴风吹倒的树木两头,在落叶的醉人的气味里,一头母狼正在生小狼。它也像女人生孩子那样,嗟叹着,嚼着身下漫血的砂土。后来,当它砥着第一头湿漉漉、毛茸茸的小狼的时候,听见从不远的洼地里,从灌木林那里,传来两响低哑的步枪声和人的叫声。
母狼警惕地听着,听到一阵短促的嗟叹声,就嘶哑而凄凉地嚎起来。
1925年
-->上一篇:让北京兔儿爷“复活”的那个人走了
下一篇:返回列表